Information-Justice|信 息 正 义

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我们不应浪费任何一场危机”。
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那场危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我们其实被困在
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
解决方案就是
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
承认它的失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
有一个“好消息”是:
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
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
都不是一个好答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译者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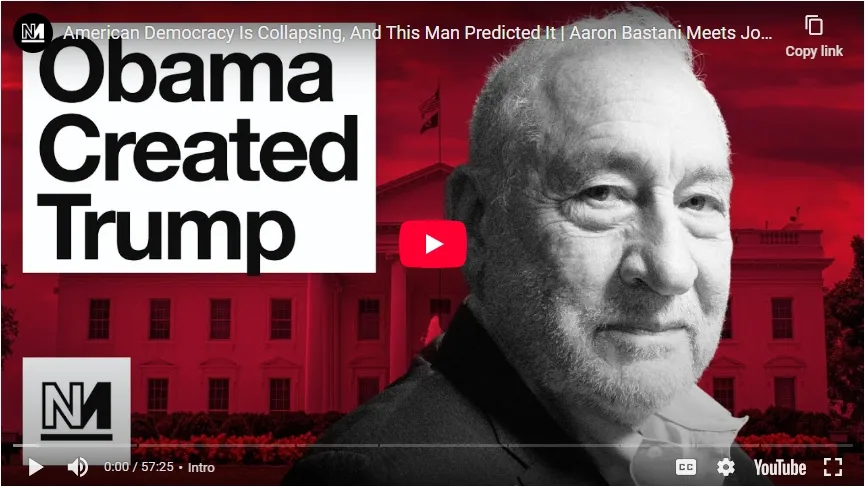
信息正义今日刊发的是播客《下游》(Downstream)2025年6月15日节目的文字纪录翻译。“Downstream”这个名字意为:从边缘性观点出发,批判主流话语结构,并提升“下游声音”,即普通人被政治与资本结构压制的视角。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是英国政治评论员、记者和作家。他于2011年与人共同创立了左翼媒体“诺瓦拉媒体”(Novara Media),并定期主持和参与该组织在油管上播出的“Novara Live”直播新闻节目。巴斯塔尼曾提出“完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自动化大幅减少了人类所需的劳动量。
受访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美国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分析师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及1979年约翰·贝兹·克拉克奖的得主。他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也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成员和主席。
长期以来,他对“涓滴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有目共睹,他所提出的预言回头看来更为真切。
自从2008年起,针对华尔街的房地产泡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金融改革的建议,对资本主义自由化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提出严厉的批评。
早在2012年,斯蒂格利茨就宣称,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社会的收入结构越来越不平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国梦是个神话”,而“贫富不均的问题终将对高收入富人造成伤害”。
这场访问是身在英国的巴斯塔尼对身在美国的斯蒂格利茨所进行的视频访谈。
他们讨论了美国民主的崩溃、斯蒂格利茨与新自由主义的推手,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之间的关系,等等。
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本有机会推行广泛的市场改革。然而,他们选择救助银行,并为大规模不平等和一种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斯蒂格利茨曾预言,这种文化最终将导致一个威权政府的出现。
他们的对话开放而坦诚,从对历史的回顾到对当下的对比,这在川普2.0的时代更具有实质上的意义。斯蒂格利茨对问题的针砭经常一针见血。不但如此,谈话中洋溢着先知性的智慧和淡定,它所提出的挑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By 临风)

American Democracy Is Collapsing, And This Man Predicted It | Aaron Bastani Meets Joseph Stiglitz
美国民主正在崩溃,
而此人早已预见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编译作品。已开通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
译:临风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Brandi
亚伦·巴斯塔尼:这些年来,我们在“Downstream”节目中邀请了很多出色的嘉宾,但今天是我第一次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对话。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我认为他还是过去三四十年来,用英语讨论这些议题最具表达力的沟通者之一。
《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让他在全球化话题上成为了体制内的吹哨人,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提出了批评。斯蒂格利茨先生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让这些缩略词(IMF、世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为全球不平等加剧的代名词。更近的是在2008年,他身处核心决策圈,参与了应对1929年以来最大金融危机时美国所采取的救助方案的重大决策。
所以我们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过去30年,过去15年,甚至是最近,尤其是唐纳德·川普去年当选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希望你喜欢这次访谈。
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欢迎做客“Downstream”。
斯蒂格利茨:很高兴来到这里。
巴斯塔尼:我们在诺瓦拉媒体喜欢保持一点形式感。很荣幸邀请你来做客,你是我们节目的首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噢,谢谢你。
异类的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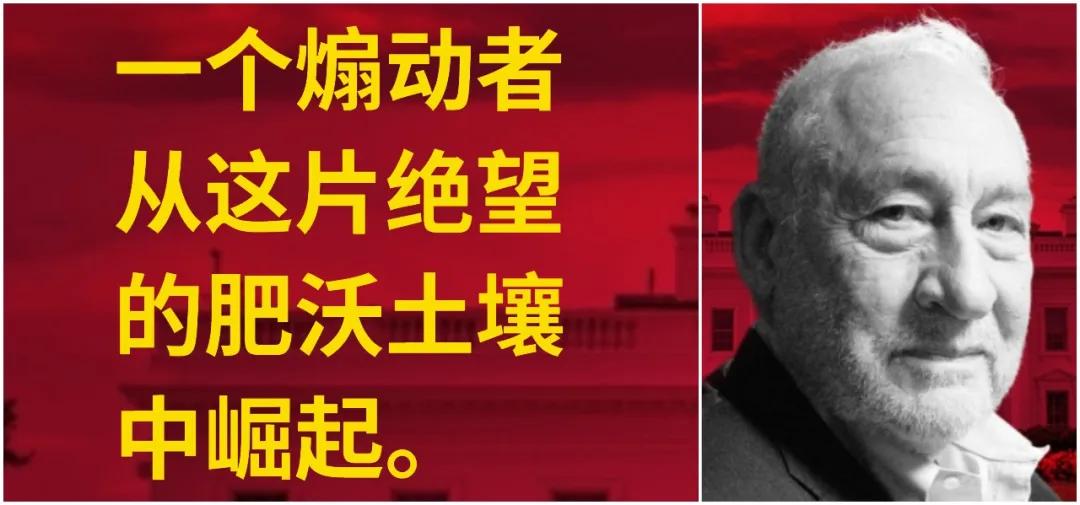
Joseph Stiglitz
巴斯塔尼:这是个非凡的荣誉。显然你最出名的书是那本出版已有些年头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本新书——《通往自由之路:经济与美好社会》(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

当然,我也会想谈谈你以前的一些著作。事实上,我想从那本书开始谈起。你曾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全球化批评者,那个时期是全球化的巅峰——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你是否会以一种近乎怀旧的眼光回望那时?你看,当前的世界经济还不错,全球经济增长,西方的生活水平在上升。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当时对全球化的批评有点太苛刻了?
斯蒂格利茨:不,我不喜欢说“我早就说过了”这种话,但我认为我当时所说的,其实预示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
我是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写的那本书,我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我写作时指出,那些全球化安排对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是不公平的,对美国的工人也不公平。那些协议基本上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益和金融利益之上的,特别是美国的。
我当时就担心,全球化背后的很多经济分析其实站不住脚。比如说“涓滴经济学”这种理念——只要把蛋糕做大,大家都会过得更好。这背后根本没有理论支持。
事实上,经济理论表明,开放贸易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工人收入下降。那些理论假设自由流动的投机资本会让全球经济更稳定。但如果你看看历史,资本的流动方式是非常不稳定的。
他们还认为开放自由贸易虽然会导致部分工作岗位流失,但会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这是对就业创造的一种过于简化的看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但我们现在也知道,即使在发达国家,创造就业也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我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工人从低生产力、与进口竞争的行业被转移到了“零生产力”的失业状态。这显然不是创造财富、改善人们生活的方式。所以,那时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实都预示了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
而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在发达国家。
巴斯塔尼:听起来你认为,你在世纪之交对全球化的诊断,与2016年之后美国以及本国发生的政治事件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因果线。那么,二十年前、二十五年前,你是否认为美国会出现像川普这样的政治人物?还是说,像你提到的那样,你当时更关注的是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你在25年前并没有这种想法,那么是什么时候让你意识到,美国政治可能会因为这种全球经济格局而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动荡,甚至在你一生中都未曾见过?
斯蒂格利茨: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民主脆弱期”,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当我观察我们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时,非常清楚,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做法,完全是在服务金融市场的利益,却疏远了社会中的其他所有人。我当时参与了很多政治层面的讨论。
比如说,在奥巴马还没有当选之前,也就是竞选的最后阶段,我曾参与一个电话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民主党应该如何应对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
电话会议中有许多来自大银行和金融市场的人。而我是少数几个“异类”声音之一,我说:“你们也应该关注美国工人和即将失去房屋的美国房主。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银行,那么经济复苏不会理想,政治后果也会非常糟糕。”
他们嘲笑了我。他们说,“哦,拜托,认真点吧。我们现在必须拯救银行。”
不幸的是,奥巴马确实执行了那样的策略。到了稍晚一些的时候,在2011年,我在《名利场》(Vanityfai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1%民有、1%民治、1%民享的政府》(Of the 1%, For the 1%, and By the 1%),这是在对应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那句著名的话——“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当时感觉,我们的政府已经变成了服务于顶层1%利益的工具。

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的文章,《1%民有、1%民治、1%民享的政府》
这也促使我写了《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这本书。而当我在2012年完成那本书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我们正在培养民粹主义者崛起的肥沃土壤。在书中,我就写到了,有可能会出现像川普这样的煽动型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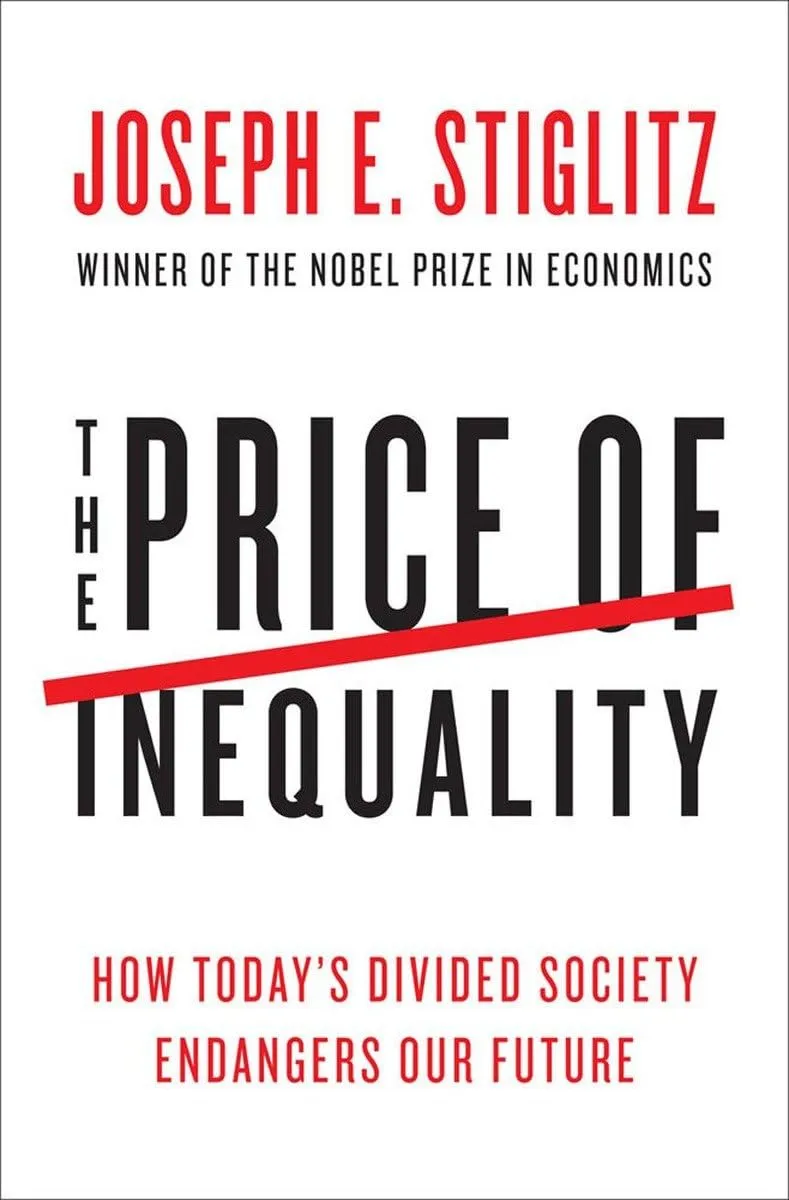
那时候,我还没有清晰地想象出像川普这样危险的人物——他的出现完全超出我们原有的认知。但我当时已经非常肯定,我们面临着一个高度风险:会出现一个民粹主义的煽动者。
奥巴马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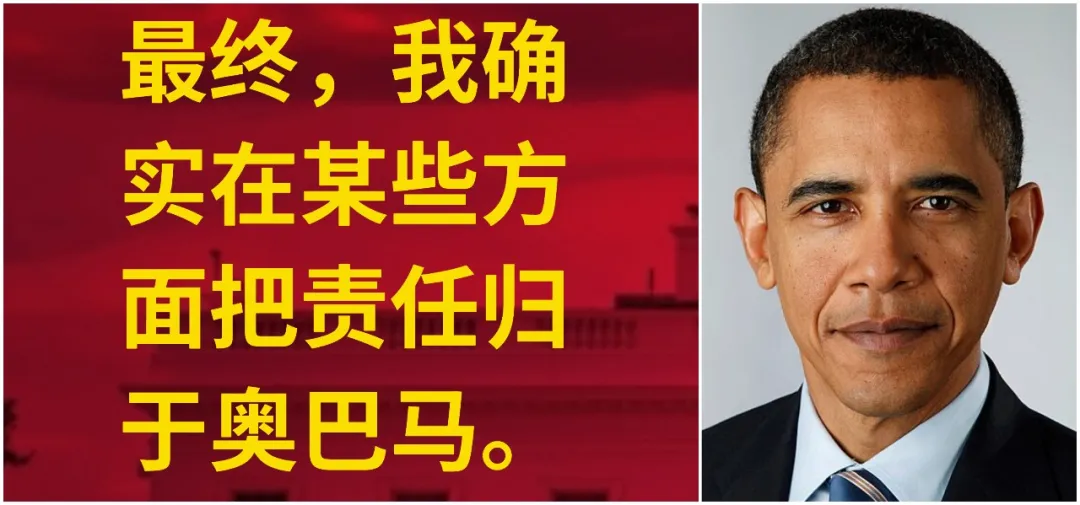
Barack Obama
巴斯塔尼:所以在2008年,我们遭遇了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尤其是对美国来说。
然后你看到政府的反应——这真的非常惊人。你当时参与的那个电话会议,应该是和像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鲍勃·鲁宾(Bob Rubin)这些人一起,对吧?所有那些金融圈的大佬。当然了,盖特纳后来成了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我记得扎克·戈德曼(Zach Goldman)好像也在那一圈。
所以你亲耳听到这些人是怎么说的,而他们完全没有兴趣考虑他们决策背后的溢出效应、政治风险。他们根本不担心那些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的问题是:因为你见证了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各种人物和性格。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这个国家里,曾经历过二战的一代政治家和欧洲政治家们,都非常害怕重蹈覆辙。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认知:政治一旦失控,会迅速堕入极端与暴力,所以我们必须避免那样的动荡、那样的崩溃。
但现在,在大西洋两岸的社会中,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历史遗产”、那种集体记忆。现在的商界和政治精英,根本不再思考政治混乱、政权崩塌、煽动者崛起的可能性。这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你说得对。我们经历了太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我们有几十年的共同繁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都在增长,而且底层增长得更多。因此,那一时期几乎孕育出一种对“美国中产阶级”的信念。
这是我成长的时代。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1980年里根上台之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确实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背离了战后那25年“社会团结、高税收”的模式——富人缴纳高税,整个社会维持某种程度的团结。
而新自由主义则压低了高收入者的税收,放松监管,可以说是“让市场自由奔跑”。而它确实“跑”了起来,其结果就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一场接一场的金融危机。
这与他们当初承诺的美好图景完全相反,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经济系统更加不稳定,社会更加不平等。但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大家就像喝了“毒鸡尾酒”一样深信不疑,即便数据摆在眼前,表明这个实验正在失败。
就像任何宗教邪教一样,他们说,“再给点时间,再等等”。而时间过去,我们迎来了2008年的又一场危机,经济鸿沟继续扩大,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下降。最终,我曾预见的情景变成了现实——一个煽动者从这片绝望的肥沃土壤中崛起。
巴斯塔尼:那你是不是认为,川普的出现要归咎于奥巴马政府?听起来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某些选择,让这几乎变得不可避免。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问题其实早在奥巴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必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问题在卡特政府时期就已开始,那时候开始了去监管化。克林顿延续了这一趋势,进行了大规模金融领域的放松监管,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这是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加剧不平等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克林顿议程的一部分。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事态的走向已经非常明确,不能再有借口。
所以,是的,最终我确实在某些方面把责任归于奥巴马。
首先,他有一个成就,那就是“奥巴马医保”(Obamacare),为大量原本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了医疗保障。这确实是一个成就。
当然,在设计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我当时就主张设置一个“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就是说,如果私人保险公司不能提供人们想要和需要的服务,就应该有一个公共医疗保险选项。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保险公司游说下被否决了——他们不希望面对竞争。
而他们不愿意面对竞争这一事实,其实应该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害怕公共选项。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功。
但他对银行救助的处理方式、未能有效帮助抵押贷款者、经济复苏计划力度不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无所作为——这些都是失败。
而在政治层面上,他也没能……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一级和地方一级发生的事情其实非常关键。他没有去加强民主党的州级和地方组织。
与此同时,共和党却在大力经营州与地方势力。所以,最终我们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脆弱,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更加容易受冲击。
巴斯塔尼:是啊,对在英国观看和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到2012年,尽管奥巴马成功连任,但在“下级选举”(down-ballot races,这里指低于总统职位的选举或地方选举-译者注)中,民主党却表现很差,选民投票率明显下降。而这15年来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右翼反而从激进左翼、甚至20世纪的左翼组织手段中吸取了更多经验,比如如何建党、如何组织群众,而中间派和中左翼却没有。
在我们转向讨论你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前,最后一个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我记得你在书里提到,你多年前曾见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虚伪

Milton Friedman
斯蒂格利茨:其实,多年来我和他有很多很多次接触。我曾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里的一名“当摆设”的自由派成员。这个研究所,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它是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智库,是所有右翼人士接受训练、灌输的地方之一。每位美国总统通常都会有一个图书馆,而图书馆往往还会附带一个智库。赫伯特·胡佛是典型的右翼总统代表,他当年在经济大萧条爆发时说,“让市场自己解决”,结果就酿成了灾难。
1929年9月股市崩盘时,他什么都没做,结果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萧条。所以他成为了“典范右派经济政策”的象征,而在胡佛研究所,他们还以此为荣。他们当时想象征性地引进少数几个自由派人物。
我当时在斯坦福教书,于是他们把我找去了,还有其他几位,比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也很乐意借此机会了解整个政治光谱。我们确实进行了很多次交流。
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为什么企业追求最大化股东价值,并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福祉。我是用数学模型来说明这个观点。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写一篇后来证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主张企业就应该最大化股票市值。我后来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做报告,介绍我的论文。我做完研讨会之后,我们站在研讨教室外面,他对我说:“乔,你错了。”
我说:“米尔顿,那你告诉我,我在哪个假设上错了?还是我的分析逻辑哪里有问题?”
他说:“乔,你错了。我就是知道最大化股东利益对社会是最好的。”
我说:“请你看看这篇文章。我花了很多功夫推导证明你不对,你能不能指出我的分析中到底哪里有错?”
他说:“乔,你错了。”那一刻非常清楚,他已经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人。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但他无法参与真正的分析性讨论。他非常聪明,也很友好,是个很随和的人,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
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点虚伪(我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更准确)。因为在他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有一个论点是: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非常重要。我确实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关系。
而他谈论这点时的语气让人觉得,他真正关心的是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只是通向政治自由的一种手段。但令人震惊的是,他却很坦然地跑去智利,成为皮诺切特的顾问——那可是一个刚刚“清洗”了几万人、强权统治的政权——并利用这种政治专制,把他的经济意识形态强加在智利人民身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政治独裁来强推他所谓的“经济自由”。
巴斯塔尼:我经常在YouTube上看到弗里德曼的视频片段。我总在想,天哪,我们真的该庆幸他没活在TikTok和Instagram的时代,因为他有一种极其吸引人的“短视频传播能力”,非常适合吸引点击率和制造爆点。他的话题简洁、抓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网红经济学”这个词,但他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学家了。
就像你说的,他后来成了一个“思想网红”。
斯蒂格利茨:当然,他早期确实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认为所有人都尊重他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修辞大师。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那些“视频爆点”有多么精彩。
被歪曲的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巴斯塔尼:是的,是的,他确实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提出的观点就特别有说服力。在你的书中你提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
这个人生活在250多年前,几乎和美国共和国建立是同一个时代。我们谈的是18世纪中期,对吧?
斯蒂格利茨:1776年是《国富论》发表的年份。
巴斯塔尼:对,就是那一年。
斯蒂格利茨:对你的听众来说,如果他们记不清,那也是我们《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
巴斯塔尼:这是个重要的年份。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借用亚当·斯密的名号来为自己喜欢的政策辩护?
斯蒂格利茨:哦,他要是在天有知,恐怕早就气得在坟墓里翻身了。如果你完整地读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确实谈到了“看不见的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好像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社会福祉。但那只是他众多思想中的一个。
你可以这样理解:他只是把“看不见的手”当作一种力量在描述而已。他在其他地方也说过,比如:“商人们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消遣还是别的什么——几乎从不会不密谋一些有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所以他并不认为商人天生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而存在的,他其实非常担心我们今天所说的“反竞争行为”。
他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当一项法规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时,它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当法规是为了企业的利益,那就未必了。他非常清楚企业如何控制国家机器,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规来谋取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寻租”。
他同样也意识到,国家为工人利益进行监管,对整个社会福祉来说是多么重要。
他还指出,企业之间几乎总是在秘密中联手,试图压低工人工资。我经常引用他这段话,来批评200年后在好莱坞和硅谷发生的一些密谋行为——这些超级赚钱的公司居然联合起来压低那些为他们创造利润的工人的工资。
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但他有一种远见,也许是对人性本质和对利润贪婪的深刻理解。但显然,他并不支持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
巴斯塔尼:是的,他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早期类似“工会权利”的观点,他谈到雇主结成联盟。而那时,工会是非法的。比如几十年后,英国南部发生“托尔普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事件,他们因为团结起来争取工资而被控罪。
所以,亚当·斯密的思想被如此严重地误用、滥用,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是被误解的吗?
是不是某种政治企图,想要把亚当·斯密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这种扭曲从哪里来的?因为如果你花十分钟去读《国富论》或《道德情操论》,你会很快发现这些事根本不是秘密。
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要理解这种误读是怎么发生的,就得意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不平等的起源”。
回顾工业革命初期,有些人确实富了起来,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尤其是那些迁入城市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人。
如果你读狄更斯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个时代有多么严酷。所以,很明显,那些你可以称之为“资本家”的人正在受益,他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来为当时的现实辩护,一整套理论应运而生,我把它们总结为所谓的“应得说”(just deserts):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配得上。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更努力,更有创新精神。牛津大学一位首席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我200年后也占据过那个席位——曾说资本家的高收入源自于“节制”(abstinence),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意思是说他们不消费,所以储蓄有功,收入是对他们节制的奖励。
于是,这套理论就这么发展起来了:不平等并不可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是所谓“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赋予不平等的“道德合理性”。
另一套理论,当然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是利用工人获取利润。
于是你看到,两种世界观在较量: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系统高效而且正当,另一方认为它是剥削性制度,最终将面临系统性崩溃。
而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亚当·斯密就被当作“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亚当·斯密才是那个“屋子里最理性的人”。
他看到了市场激励机制的好处,也看到了市场可能造成的剥削,因此他主张要有政府监管。他还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比如提供教育。
他还支持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亚当·斯密其实非常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他并不是那种单纯激进的剥削论者,而是一个试图平衡地看待市场经济优劣的人。
巴斯塔尼:是的。如果真正读一读亚当·斯密的话,我觉得现代人会发现他其实更接近中左派。而马克思呢,公平地说,他自称是实证主义者(empiricist),但他同时也是个辩论者、煽动者,对吧?
他是在一个历史关键时刻试图写出一部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檄文。而斯密并不是做这样的事。但你说得很对。
你读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论的发明者——译者注)和亚当·斯密时就会发现,他们说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马尔萨斯的意思几乎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吃不饱而饿死,那就是自然规律,就该那样。
斯蒂格利茨:就是认为这是系统的“均衡”部分。
美国需要FDR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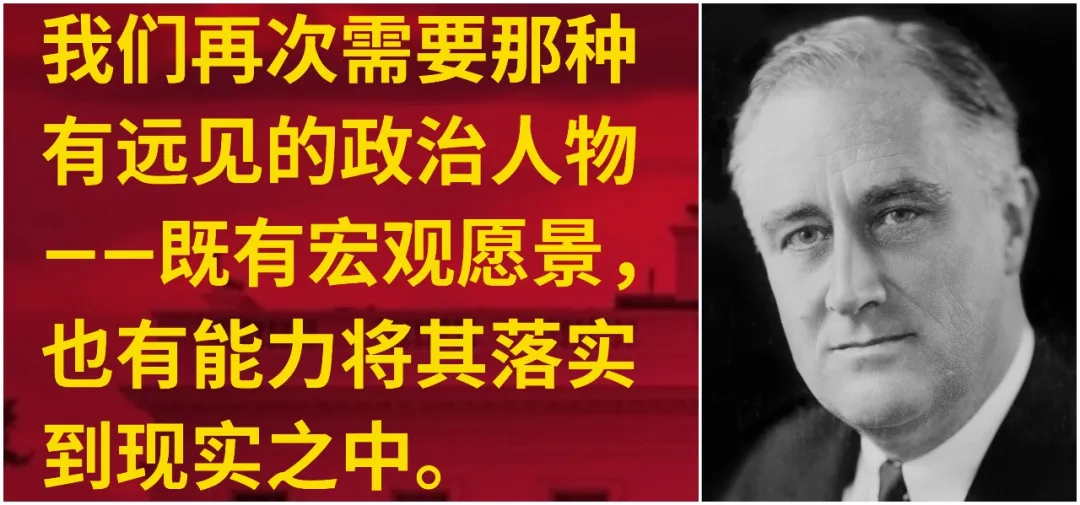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巴斯塔尼:是啊。然后这些思想家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一致,在马克思的对立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美国现在需要另一个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吗?
斯蒂格利茨:是的。你看,FDR是对“大萧条”作出回应的领导人。但他当时的回应不仅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刺激经济”,他还指出我们社会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社会保障体系。
于是他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他还说,工人的议价能力太弱,他们被抛弃了。因此,我们通过了后来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的法律,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
这些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举措。他还强调政府在投资中也应发挥作用。虽然美国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力供应。他指出,市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政府就要来做这件事,为全国提供电力。
他还说,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强调我们拥有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我们也应该有经济权利,比如免于饥饿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他对国家角色进行了全新的构想。
他也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会有些人主张小政府,有些人希望维持不平等,他们会反对我。但他有一种不同的社会愿景,他坚持不懈,推动这个愿景,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
如今,几乎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再次需要那种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既有宏观愿景,也有能力将其落实到现实之中。
奥巴马的幕僚长曾经说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但奥巴马确实浪费了。他所做的是拼拼凑凑,主要是挽救银行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社会。他错失了那个时刻。
而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关键时刻——但这次,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川普践踏了我们的民主制度和法治,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机制是多么脆弱。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谓的“制衡机制”,也许还能撑住,我们希望它能撑住,但它们太脆弱了。此时此刻,我们本不该靠祈祷维持秩序,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只能靠祈祷了。
巴斯塔尼:你觉得为什么进步党派就这么难再造出像FDR那样的政治人物?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在英国也是如此,而且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现象。就像你说的,奥巴马掌握了一个危机的契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选票支持——那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总统候选人,我会说是自肯尼迪以来最有魅力的美国政治家(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里根,但肯定属于那个级别)——然而他却没有兑现一个整体性的政治项目。
你现在在英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施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也是这样。
你刚才用了“拼拼凑凑”这个词,说得太准确了。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世界的国家中,进步党派都没有真正推动你所说的FDR式议程?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他们?
斯蒂格利茨:我想可以从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说起,那时我们经历了一个大缓和时期。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温和”的年代,人们试图达成共识。也可以说,我不想用反弹这个词,但认为FDR太过尖锐了。
人们当时说:“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别再提‘阶级斗争’这种东西,那是过去的事,是旧的共产主义语言,我们把那些留在过去吧。我们是一大家子,过得挺好。”
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一大家子”,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那种信念、那种意识形态、那种对“我们是一家人”的希望,限制了政治家们敢于采取的行动。他们不愿意显得太激进。
而FDR当时面对现实,说:“我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激进,我们就无法走出大萧条。”他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必须做出抉择。
这需要一种胆识。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有魄力的领导人的,比如美国的AOC(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还有一些州长,我认为他们有能力提出一套新的、进步的议程。这与过去的做法不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我们不需要复制19世纪的斗争,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策略。这需要一种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时刻,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体行动。
而很不幸,我们现在的现实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变革。
巴斯塔尼:是啊,这是政客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对吧?那我接下来就带着点怀疑主义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我基本上同意你刚才说的所有观点。
但对那些看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或者在英国看GB News的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说: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你对FDR的分析是合理的,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个人债务比过去高得多,主权债务也比以前高得多。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增长了,只是靠债务驱动的杠杆式增长——基本上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是这样。
美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增长模式。人们谈论川普时期的经济增长,但你看看财政赤字,那也不是靠私营部门带动的真正繁荣。
在英国也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你把大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话。所以,这和1930年代的情况完全不同。面对如今的高债务、零增长,甚至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我们是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老年护理和医疗成本都更高了,你会怎么回应这些质疑?
斯蒂格利茨:我首先会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具创新力的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为什么比250年前高这么多?根本原因是科学进步,以及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集体合作。
我们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如大型企业,还有更广义上的社会制度,比如制衡机制、法治制度、如何让民主运作起来。而且我们也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良治(good governance)的原则,什么是劣治(bad governance)的表现。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们实际上比100年前处于更好的位置。关键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并引导这些知识,为社会大多数人(而不仅是少数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
我认为,我们其实被困在一个长达45年的失败实验之中。对我来说,解决方案就是从这个实验中挣脱出来,承认它的失败。这个实验当然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实验,也就是“自由市场会带来更高的增长”,“通过涓滴效应让所有人受益”,以及“市场本身是稳定的”。
我们已经对这些假设做了充分的尝试,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国接一国地失败了。所以对我来说,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其实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可以开始构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体系。我并不认为这会容易,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你必须说服大量民众。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几十年来都被“洗脑”了。他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再多给它一点时间,这个制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终将奏效。但最终,他们开始失望了。
而这种失望正在把他们推向威权民粹主义。你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好消息”是:川普正在让大家看到,威权民粹主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好答案。
巴斯塔尼:是啊,很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自我”的崩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你可能会指出一个市场失灵的例子,或者是一个负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都是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而人们的反应却是:“这是社会主义”,或者“这是因为移民”。
因为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嘛——这个制度是会自我纠正的,是会自然达到均衡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呼吸的“新鲜空气”。
我觉得你说得对。这正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最终的答案却变成了右翼威权主义。我还是继续站在怀疑者的立场说话。
特别是在英国语境下,比如GB News的观众可能会说:好吧,斯蒂格利茨先生,斯蒂格利茨教授,我们确实想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但我们现在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接近100%了。我的个人税负也很高。
我孩子上大学就背了5万英镑的债。我们去年财政赤字是1200亿英镑,利息支出高达1000亿英镑,这在英国是非常高的。
那你说我们要加大投资,比如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请问这笔钱要从哪来?
你是主张加税吗?还是你会削减其他领域的开支?
斯蒂格利茨:首先,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债务与GDP比率比现在还要高,远远高于现在。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止步不前。
接下来的几十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时期,那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30%以上降到了45%以下。只要经济增长,债务与GDP的比率就会下降,因为GDP在增长。英国的债务与GDP比率当时甚至更高,但后来也降下来了。
你们的情况更困难一些,战争对你们打击更大,破坏更严重。我们只是推迟了一些投资,而你们遭受了很多实际的损失。但这证明,即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出增长战略。现在你进一步追问我具体措施,我认为,增加税收有很大的空间。
我在美国对此研究得很深入。我知道我们在十年期内(我们通常以十年为窗口衡量)确实有能力提高税收,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设定的税率与我们实际征收的税收之间有巨大鸿沟。
尤其是企业,逃税避税现象非常严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它为通过避税天堂和保密制度进行逃税和避税提供了“绝佳平台”。但我们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环境税,通过减少污染来改善社会。
还有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例如,金融交易,尤其是短期交易,会造成巨大波动,扰乱经济。所以,在金融交易税方面,我们也有很大空间。
在美国,资本所有者的税率比一名水管工的工薪税率还要低。如果我们仅仅对资本进行公平征税,就可以筹集几万亿美元。而如果我们实施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的合理实现,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性改革,我们将再次能够筹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
所以在美国,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对研发、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的公共投资。这些投资将带来一项增长议程,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引领我们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西方可以向中国取经吗?
巴斯塔尼:你在书中谈到中国。我想把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
过去35年来,中国是如何管理其经济的?西方能从中学到什么?
斯蒂格利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自我定义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把这些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中国跟任何其他经济体都不一样。
有些人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也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企业部门。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深远得多。因此它确实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大的角色。
我认为,从中国作为经济体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里我们不谈民主等其他方面,仅仅谈经济上的成功。
首先,中国有一个愿景。它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我们的生活水平要低于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大多数国家从未认真自问过的问题。而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他们说:“没有理由我们不能拥有与任何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
这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开始思考: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们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我第一次与中国方面会面是在1980年。
我第一次访问是在1981年,从那之后就一直持续进行对话。他们希望从一切可能的来源学习。
他们听取不同的观点,然后将其整合到自身的框架中。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新性的理念。我现在没时间一一讲述。
其次,有一点很明显:他们重视对人的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他们派出数十万人前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去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工程师。现在你已经看到了这些投资的成果。
几周前我还在中国,参观了他们的一家新汽车工厂,机器人在组装汽车,几乎没有人类操作。非常惊人。
工厂里大多数员工并不是生产线工人,而是工程师。他们已经从一个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拥有工程与高技能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这是过去45年来的惊人变化。
第三,他们进行了规划,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如何实现这个愿景?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
如今美国终于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在《芯片法案》(CHIPS Act)中,美国承认我们缺乏生产现代经济核心组件——芯片——的能力。
还有《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承认我们尚未为绿色转型做好准备。
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广泛的产业政策。川普正在做的,是将贸易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他想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在做的事。
但他执行的方式非常鲁莽、无知,并且具有破坏性,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经济秩序都是如此。这使人质疑他是否真能取得什么成果。其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是巨大的。
对美国经济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从中国身上学习和研究的。当然,中国拥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规模——如果你有13亿人口,你的国内市场就是一个大市场。
这个没有边界的大市场带来了很多优势。
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来衡量,也就是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价格结构的国家时所使用的方法,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使得他们有了巨大的机会,继续推进他们的发展战略。
巴斯塔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感谢你参加“Downstream”节目。
斯蒂格利茨:谢谢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